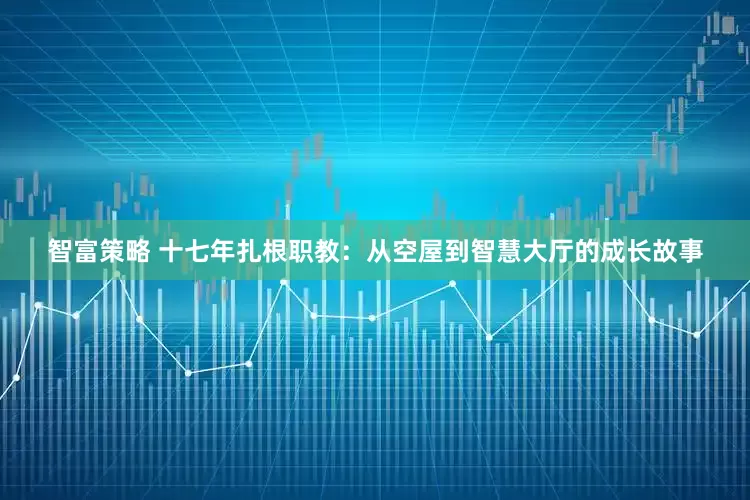
每次走进学校的智慧大厅,感应门随着脚步轻轻滑开,阳光透过玻璃,细碎地洒在地毯上。我总会在这里驻足片刻。十七年前,这里还不是智慧大厅,它只是一间水泥裸露的空房间。而我,就是在那间空房里,敲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颗钉子——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颗。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,十七年过去,我依然在这里。所有的青春、成长与热爱,都藏在这片唯一的土壤之中。
2008年的初秋,冯校长领着我穿过学校操场,往教学楼深处走。那时我刚走出校门,捏着衣角跟在他身后,心里像揣着只小兔子——这是我第一次以职场人的身份走进校园,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着陌生与期待。走到那间后来被称作“图书馆”的空屋门口,冯校长敲了敲半掩的办公室门:“这是新来的小张,以后就交给你们部门带了。”时任部门负责人张校长从屋里迎出来,笑着握了握我的手,转身就指向墙角的扫帚和水桶:“来得正好,先搭把手把这里拾掇拾掇吧。”我愣了一下,看着眼前的景象——没有欢迎仪式,没有工作交接,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办公室的全貌,我的职场第一课,就从拿起扫帚开始了。
后来才知道,我来到的是学校的新校区,就是我未来要扎根的地方。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这地方要改成图书馆,从无到有,慢慢弄。”现在想来,那天的劳动或许是最好的“入职礼”——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:工作从不是纸上谈兵,而是从弯腰扫地、抬手擦窗这些实在事做起的。图书馆完善的初期,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。那会的我,对着空荡荡的屋子琢磨怎么规划区域;没有成型的方案,就跑到邻校的图书馆偷偷观察,看别人怎么划分阅览区和藏书区,回来就在纸上用笔画图,擦了改、改了画。
展开剩余75%初期,最费功夫的是图书录入。一万多册书堆在墙角,像座小山,每一本都要核对ISBN号、登记分类、贴磁条、录入系统。我在临时支起的办公桌上坐了整整两个多月,白天对着电脑屏幕敲编号,晚上回家闭上眼,眼前都是密密麻麻的条形码在晃。就这样边学边做,从前期录入到给书架贴上分类标签;从在门口装上门禁系统,到制定《借阅须知》贴在墙上,那些曾让我犯愁的“空白”,一点点被填满。现在每次走过智慧大厅,感应门滑开的瞬间,我总会想起入职那天握着扫帚的掌心温度,想起那些在空房里搬书、贴画、和学生一起整理书架的日子。
图书馆运行大概一年多的时间,一个寻常的午后,时任教务负责人张校长突然出现在门口。他没说什么,只是绕着书架走了一圈,翻了翻借阅登记本。临走时他笑着说:“小张,这地方被你盘活了,比我想象中好十倍。”我当时只顾着紧张,捏着衣角说不出话——在第一份工作里得到认可,那种开心像是被糖泡透了。不久后,我被叫到了张校长的办公室。他开门见山地说:“教务处缺个助理,我想让你过来。” “校长,我不行的!您看我这性格,整天和学生打打闹闹,教务处的工作那么严谨,我肯定做不来。”那时候的我,对“教务”一词充满敬畏,更怕自己做不好这份“转岗”的工作。
他没急着说服我,只是讲了个例子。他说“人就像图书馆里的书,不翻开看看,怎么知道里面藏着多少故事?”他看着我的眼睛说,“你把一间空屋变成学生喜欢的图书馆,说明你有耐心、有办法,更重要的是你心里装着别人——教务工作看着是排课表、整理档案,说到底也是为老师学生服务,你肯定能行。”那天走出办公室时,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。我在操场边坐了很久,想起刚入职时看到的一句话:“一份工作做久了,不是靠新鲜感撑着,是靠责任感。”最终,我走进了教务处的门。我告诉自己:既然这是我的工作,那就别怕改变,试着把每个阶段都走好。
刚开始的日子,比想象中更难。教务处的办公室永远堆着高高的文件,课表上的每一个格子都像数学公式,错一个数字就会引发连锁反应。那会还是手工排课,我把两个班级的实训课排在了同一个车间,任课老师找到办公室时,我脸涨得通红,话都说不完整。张校长走过来,拿起红笔在我的草稿纸上画了个流程图:“你看,把实训室比作“舞台”,老师是“演员”,学生是“观众”,排课就是给他们排演出顺序,想清楚了就不难。”渐渐地,我摸到了教务工作的门道。
一晃十几年,教务处的负责人换了几任,搭档的助理也走了又来,只有我还守在那张办公桌前。期间不是没有朋友劝我:“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,不觉得局限吗?出去看看说不定有更好的机会。”我每次都笑着摇头——他们不懂,这所学校早就不是单纯的“工作单位”了。我看着一届届学生入学、毕业,看着年轻老师变成资深骨干,看着校园里的树从幼苗长到参天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刻着我的记忆,这份唯一的工作,早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有人问我:“十几年做同一件事,不觉得枯燥吗?”我总会想起那间曾被改造成图书馆的空屋,想起入职那天拿起扫帚的瞬间——就像盖房子,地基要打十几年才能稳,教务工作看似重复,实则每一年都在为学校的教学大厦添砖加瓦。而我,作为这场漫长建设中始终在场的参与者,这种踏实感,让人心里安稳。
2019年夏,我因生二胎休产假,离开前将记满工作流程的文件收好,自认是岗位“不可或缺”的“老人”。产假期间,同事和我提到新助理的表现,我顿觉自己并非不可替代,陷入焦虑。2021年返岗,才让我明白工作如接力赛。那时,我在笔记扉页写下“做高规格螺丝钉”,开始琢磨优化工作:按逻辑分类档案、结合时间合理排课等。
这两年,AI、大数据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耳边。有次听讲座,专家说“行政工作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领域”,我心里咯噔一下,危机感像潮水般涌来。但转念一想,机器能处理数据,却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——就像当年在图书馆,学生需要的不只是一本书,还有递书时那句“这本书很适合你”的默契;现在做教务,老师需要的也不只是排好的课表,还有一句“我知道你这周有培训,已经帮你调好了课”的体谅。
学校一直倡导教师终身学习,以前总觉得那是任课老师的事,现在才发现,每个岗位都需要“充电”。读了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》让我学会了“要事第一”,《非暴力沟通》帮我更好地协调师生矛盾,那些以前觉得晦涩的理论,慢慢变成了工作中的“方法论”。我想,就算只做这一份工作,也要做个不断成长的“职场人”。当然,最幸运的是加入新网师的共读会。同样一本共读书籍,有的人看到了是课堂的温度,有管理者看到了团队的协作,而我看到的是“服务的价值”。教务工作的意义,不在于多耀眼,而在于像空气一样,无声无息却不可或缺。
就像这所学校于我,是唯一的职场,我于它,也该成为那道不能少的风景。十七年,足够让一间空屋变成智慧大厅,让一个懵懂的新人变成沉稳的“老教务”,也让我渐渐明白:所谓成功,未必是跳得多高、走得多远,也可以是在一个地方深深扎根,把一份工作做透、做活、做出温度。
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